2018年12月30日 13:51:17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选票”之上。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什么?尽管表面上看是实足的贸易摩擦,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具有文明性,分别是中西方文明各自演化的产物。正是因为具有文明性,这两种模式都具有可持续性,不管两者间发生怎样的竞争和冲突,谁也改变不了谁,各自都会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表现为两国之间,但根源来自美国内部体制,是美国内部体制消化和应付不了其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而执政者把此“外化”为贸易摩擦。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都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其中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关系千丝万缕,共生共存。
不过,在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中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一政治经济学概念到罗马帝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迈入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即开始把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经验事实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1)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
(2)政治秩序的重建。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到了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中世纪)的后期,欧洲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实质上处于自治状态,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和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
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便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形成中央权力的动力。
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形成了欧洲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统一国家的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
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在很长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欧洲,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
政治权力和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
政治权力“中央化”的过程也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充满暴力。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到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众多政治思想家、社会学家研究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则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但随后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而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而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而且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则成为资本的牺牲品。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起源于欧洲。无论哪里,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其“初心”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人们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
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过程。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至少有两个。
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
第二个变化源自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工人阶层满足利益的过程。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均衡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
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19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
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特(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特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不过,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选票”之上。
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
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
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到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到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是需要人们观察的。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也困难重重。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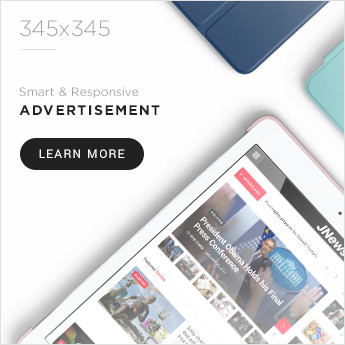













 公安部:
公安部: